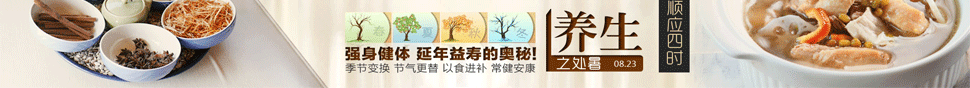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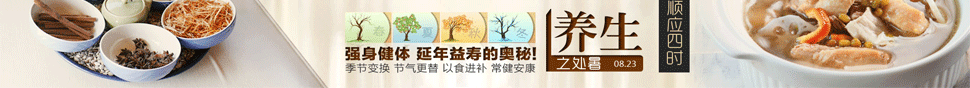
在遥远的古时,有一位医生,他的药方总是药味繁多,用量也大,因此被人们戏称为“某大包”。有一天,他家里的亲人病了,他开了一剂药方,取回药来后发现少了几味药。他立刻亲自去找药房交涉。药师仔细核对后,确认说:“先生,你开的30味药,一味也不少哇。”这位医生却回答说:“哦,是这样,正面写不下了,还有3味,写在背面呢!”这不是一个笑话,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位医生因此又得到了一个“三十三味”的外号。这位医生用药的独特风格让人印象深刻。他的处方不仅药味多,用量大,而且常常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他的外号“某大包”也因此流传开来。人们一提到这个外号,就会想起他开药的习惯。
那么,究竟一张方子里面用多少味药好呢?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最早提出了一个标准:“治有缓急,方有大小……君一臣二,制之小也,君一臣三佐九,制之大也。”也就是说,君药(主药)加臣药(辅药)共3味的,为小方;君药、臣药,再加上佐使药共13味的,为大方。这里说的3味、13味,不过是例举而言,差不多这个样子就是了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历代有代表性的医家的处方。汉代的张仲景,是后世公认的“医圣”,他的著作《伤寒杂病论》方子一共有二、三百首,至今常用的还有近百首。书中诸方用药从一味到10味都有,大致以用7味药者为多,很少超过10味者(丸方薯蓣丸,用21味,鳖甲煎丸23味,可谓绝无仅有者)。皇甫谧说:“仲景垂妙于定方”;张洁古说:“仲景一部,为群方之祖”;韩飞霞说:“仲景方何等简洁”;近贤任应秋评价:“法随证立,方依法制,药味无多,配合得宜,经历二千余年历代医家的临床验证,疗效均甚确切,只要辨证准而用之,无不如响斯应,实为方剂学中无出其右的典型。”都是允当之言。较仲景生活的时期稍晚,被后世誉为“外科鼻祖”的华佗,据陈寿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载,其用药“不过数种”,可见其处方也很简洁,他用针“亦不过一两处”,疗效很好,不象今天有的医生像插秧苗一样在病人身上胡乱扎。金元时期的名医李东垣,以《脾胃论》、《内外伤辨》著名,其用药之道颇为丰富。他创制的补气升阳和中汤,用药多达16味,清神益气汤、清暑益气汤亦各用15味。后世的医家如韩飞霞、徐灵胎等对此颇有微词,甚至有人称李东垣用药“如韩信用兵,多多益善”。清代名医叶天士,是温热学的开山鼻祖,其用药颇为精炼。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中,余案中以一方只用6味药的居多。近贤程门雪因此赞叹:“六味之中,咏涵不尽”。近代名医丁甘仁的用药每方大致在12味左其右用。药之道,犹如一位高明的指挥家,善于调配各种药物,如同指挥家调配乐队一般,奏出了一曲曲治病救人的优美旋律。我的看法是:用药要看病情的需要,当多则多,当少则少,没必要也不可能追求一律,但是,大致上也应该有一个“谱”,这个“谱”,还是以《内经》讲的少则二三味,多则十二、三味为宜,为什么很多医生提起笔来就收不住,要开很多味药呢?我的体会,毛病就出在以下几方面:一是急于见功。医生想三下两下把病给治好,不过万事万物都有个规律,通过多开些药去追求疗效,是不可取的。二是对药物的功用与弊端认识不够。对药物要“拿得准,唤得应”,“如臂之使手”。据金元四大家之一,毕生以善用汗、下、吐法攻邪著称的张子和称,他最拿得准唤得应的药也不过10来味而已,可见知药之难,为此有的医生甚至亲口尝药,以了解药效药力。三是囿于现成的套方套路。前人方用多少味,我悉数照搬,老师治病用什么方子,我也什么病什么方子。实际上,前人所拟之方,有的是从多方面设计的,如五积散,而病只有一积、二积,如六郁丸,而病人只有一郁、二郁,是不是就非照五积、六郁那样用药不可呢?至于师徒相承,赶巧老师正好是“三十三味”,那我也“三十三味”,我的徒弟将来也“三十三味”,则相沿成习,不可收拾矣!#百万创作者计划#
